当前位置 : 中国机器人峰会 >> 大会新闻
发布时间:2017-06-14发布人:中国机器人峰会
非交流难见进步,惟科技予人自由。第四届中国机器人峰会于5月16日举行了一场囊括海内外机器人专家的高端访谈,访科技前沿,谈未来发展,嘉宾争相提问,专家面对面抢答,前沿热点轮番轰炸,气氛火爆,邀您共享。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黄广斌,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张建伟,国家芜湖机器人产业集聚区领导小组组长张东,IEEE RSA候任主席席宁,浙江大学现代工业设计研究所所长孙守迁,日本名古屋大学微纳机电系统实验室主任福田敏男,俄罗斯斯科尔斯沃基金会机器人中心主席Albert Yefimov,七位大咖共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发展趋势。
刘进长:
总的来讲,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还是两个不同的分支,但是这两个分支又是不可或缺的,是不能分离的双胞胎。所以,我们国家无论从机器人还是人工智能角度都设立了相关专项,对这方面做大力支持。

主持人刘进长
时间非常宝贵,我把提问的机会让给咱们下面的听众,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想跟在座的专家交流的,这个机会特别难得。

嘉宾提问
观众1: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和这么高端专家讨论,我想咱们这个会从开始到现在,大家都在谈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我想就人工智能的问题向专家做一个请教。现在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大家都在谈深度学习。今天高端访谈的主题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那我想问一下深度学习,特别是这个Alphago,它的硬件是1000个CPU,200个GPU,要消耗20万瓦的电力,这么一个硬件什么时候装到机器人里面去?第二个问题就是作为工业机器人来讲,如果真的把深度学习装进去以后,那么在某一时刻出现了“黑箱”问题,这将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专家,有没有办法解决?
刘进长:这个问题由日本的专家回答。

孙守迁(左)、福田敏男(右)
福田敏男:
我认为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原先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对于深度学习,花了35年的时间,才做到这一点,那么关于AI,怎么样让机器人更深度学习,这是以一个域为基础的思路。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话题,还是要涉及到这样的一种深度学习的内容。我们确实可以探索它的外延,如果你有体验的话可以有很好的探索,没有体验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我们人类有更多的学习的能力,我们可以在学习到的各种知识的基础之上调整我们的行为,这个没有问题。这是很大的差别。
你之前也说到,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有1000单元的CPU,可能这个太多了,不能整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小,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比方说2.45的变化,就是说设备可以到一个时间点,它的学习能力可以超过人的智商,可能超过我自己,然后超过其他的人,这非常有趣,确实是可以考虑的。
我们可以去考虑这样的情况,但是未来这样的事情如何展开,我们想象一下,细节不得而知。但是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仍然还是这样的态度,但是想到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有趣的。谢谢。
刘进长: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庞大的计算机什么时候装到机器人上?请我们这位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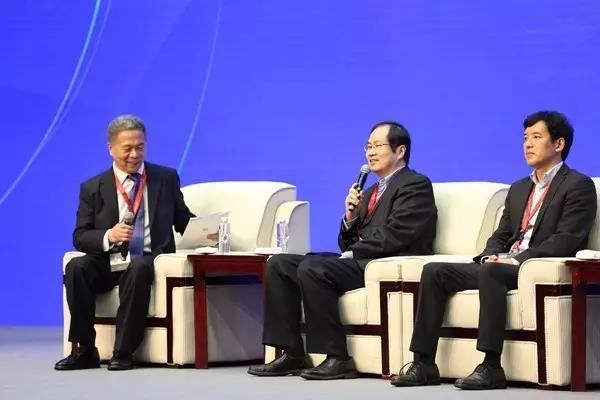
刘进长(左)、黄广斌(中)、张建伟(右)
黄广斌:
这是一个讲机器人安全的问题,一个是讲机器人和人比,是机器人快还是人快。我们看深度学习,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深度学习存在几十年了,六几年就提出了,那时候没有很好的实现方法、计算环境,没有技术实现。但是从机器学习来看,每15年是一个机器学习的周期,50年代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提出的时候,很多人争论,好多人不信,包括后来很多人工智能大咖都反对人工智能。所以到60年代,人工智能进入了冬天。到80年代中,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又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的话,大家觉得又怎么样,觉得也就是这个算法而已。
2010年开始,我认为是真正的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或者机器学习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的真正到来,并不是说这种技术就一定能永远继续下去。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存在问题的地方。但是在没有更好方法出现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很好的方法。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比如深度学习,用得比较多的是动态的概念。它的概念也在变化,早期的深度学习,是一个黑箱子学习,不是透明的。所以人们为什么不得不一层一层分开,庖丁解牛式的,现在相当于已经变得更加清晰。所以,这是最早期的深度学习。
后来,就是多个机器学习组合是深度学习,再往后发展,应用越来越复杂,你的数据越来越复杂。再往后是多个机器学习系统子系统的组合,像我们现在系统有这个子函数、那个子函数,我们现在讲的深度学习已经不是以前讲的深度学习,这个深度学习本身是多个算法的组合,比如卷积神经用图片来处理比较好。
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不同的方法,只是跟了一个通用的名词,深度学习,打开看还不叫深度学习,但是从资本运作,公司的运作,包括好多本科生毕业,其实还没有深度学习的经验,他开一个公司也叫什么深度。其实,我认为这是概念的办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Alphago现在用了很多机器,因为没有办法,再过多少天,可能过10年,就不要这么多机器,这么多资源。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学习,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算法,其实不是很有效的。我们过去其实很多年,在算法上都没有多少的改进,更多是填补应用的空间。所以我说其实人工智能,像今天早上讲的,我认为人工智能属于黎明前的黑暗,会有更快的,更高级的技术出来。只是现在还没有,所以这种技术出来之后,又不一样。那么我其实把这个智能放在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的同一级别,其实就是智能革命。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黑盒子,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我们讲人工智能是人创造的智能,将来还有更有趣的事情会出现,我们通常会把机器学习化归人工智能,但是我觉得机器学习是单独一个方向,还有我们会有越来越多情况需要机器本身学习,好多情况下,我们人还很难控制。所以人工智能,我认为是人可控制的智能,人创造也可以控制的功能。如果机器学习之后,很多情况是你不可控制的,那这个情况将变得更可怕,这就不是黑箱子的问题了。像日本朋友提的,孩子一出生都是天真无邪的,但是跟坏人学就学坏了,机器人也学习人的行为,所以机器学习就有学坏了的,所以人工智能有正面和反面,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可控的,将来可能有反面的存在。谢谢大家。
刘进长:这位女士。
观众2:
我是科技日报社和中国科技网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前不久霍金来到中国,他做了一个演讲,他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表示出极大的忧虑,他提出来是不是要放慢人工智能研究的脚步,先一起坐下来解决一下有关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这个各位专家怎么想?紧接着这个问题,是阿西莫夫的粉丝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机器人三原则将来能得到遵守吗,机器人三原则是不是已经被放弃了,或者说它与机器人发展已经产生了冲突?如果是,这种冲突有调和的可能吗?如果不是,是否恰恰证明了阿西莫夫的远见?我的问题完了。
刘进长:先请你来回答。

张东(左)、席宁(右)
席宁:
首先,担忧现在有点过早。我们现在做人工智能的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还有多难,还有多少问题没有解决。刚才说到深度学习,虽然深度学习展现了一些前景,语音识别、模式识别。但是远不止我们真正对智能机器人的要求,我们还有很多的连续学习,还有很多的机器人的记忆等等都没有解决。这些都是现在我们做服务机器人,做医疗机器人急需的人工智能的技术,还远没有到我们有一个机器人完全代替我们人类。虽然机器人的计算能力,在下棋和个别领域超过了人,但是机器人的发展远没有达到跟人在智力体力竞争的阶段,所以说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当然从现在起,我们要一方面研发我们智能机器人,另一方面考虑到伦理问题,并行的接触,包括我们阿西莫夫的三原则,我想随着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应用的越来越多,三原则可以发展到30原则,300原则,3000原则,把道德约束起来,我想我们会找到很好的方案。
刘进长:谢谢,还有没有想补充的?

孙守迁
孙守迁:
补充一下,我们的朱书记谈过要从机器人教育角度谈学科建设,我离开机械系的时候,一直跟设计师们在一起,这个就是关键的一点,就是技术专家需要跟更多学科人在一起。
我的周围有艺术家,有研究美术、艺术的人,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设计更有人情味,还有搞情感计算的人。我觉得机器人不是仅仅是我们理工男的事情,还有更多的人加入。我觉得联盟要扩大,以后张艺谋也可以参加,在印象西湖当中我是评委,就是考虑升降台要不要用相关的机械工程原理、液压系统,讨论这个问题。也要考虑,泄露是否会污染西湖湖面,可以结合起来。
黄广斌:
我回答一下。2015年我在牛津大学机器人实验室做报告的时候提到这个,其实现在是可以讨论一些问题,哲学家可能考虑一百年,一千年,我们搞技术考虑十年、二十年。
长期来说,比如我们现在讲这个事情,三十年之后我们用特殊材料做出一个我来,肢体、语言和我差不多,我讲完之后,这套都已经机器学习学完了,这个时候同样的东西可以在纽约播放,机器人做的东西跟我一模一样。现在我们要搭飞机24小时到纽约,30年后可能就是智能穿越了时空,已经到了纽约,同场开讲。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存在的,而这个时间不会太长。马云说,30年后CEO会被取代。我们团队20个人,做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我认为30年过远,其实不用30年,像现在很多炒股的失业了,机器代表几百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智能可以穿越时空。
第二,将来会有新材料。这个材料,从大局来讲不是机器有没有智慧,它是有智慧的,只是材料不一样。我们探究化合物或者石墨烯,就是想石墨烯能不能变得智能,我们已经开始考虑这个事情。我刚刚提了一个很大的项目。所以从霍金角度来说,他是对的。
另一方面,机器人有达尔文进化论。几千年前,或者几百年前,我们骑马射箭,但是后来放弃了,将来有无人车的时候,现在大家开车技术都不差,尤其是女士,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但是30年后,无人车在路上开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好多能力我们都没有了,开车的能力也没有了。当然说你也能开,但是你发现你的反应能力已经不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会受到机器人的影响,我们会失去一部分能力。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有进化论的功能。
我觉得三个定律不是问题,不应该公开谈,因为就应该是基于传统机器人1.0,就是以自动化为主,我们编程赋予机器人智能,但是有一点我们做科技的总想创造极限,突破极限,总想看我们能不能让机器人本身创造智能。所以当机器本身有自我创造能力的时候,其实很多情况下,它已经不是在那个三个定律当中考虑的问题了,已经形成了另外一个智能体社会,就是人和人下棋,人和机器下棋没有区别了。机器和机器之间形成一个智能体。不是说人的智能穿越时空。
我觉得霍金讲的东西都有可能实现,从伦理上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提前考虑,但是科技角度来说,很难考虑一万年之后。但是,我们从五年十年考虑差不多,从哲学家角度来讲,我觉得他是对的,所以我也经常会在微博上提到这些概念。谢谢。
观众3 :
我问两个问题,香港从5月1号开始,像我们所有劳工一小时差不多40块钱,我委员会下面有300家养老院,现在老板痛苦在哪里?请一个普通的护工要16000-18000港币,很痛苦。我是半年前开始学习机器人的,我想问张建伟,我知道你在深圳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我希望找到服务机器人的合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张秘书长,你们芜湖是我们中国走得最前的一个基地,然后你又是组长,我很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和你们合作?

黄广斌(左)、张建伟(右)
张建伟:
这说明服务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在未来的社会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具体的刚需,这个例子非常好。刚才也提到我们人工智能,我们机器人技术,远没有达到真正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我想在助老助残这方面一步一步来,现在如果做大规模的护工机器人还需要10-20年时间,就是先做多功能轮椅、变化的床,或者是给老人喂饭、拿东西,一个一个的功能我们可以按照具体的应用分类来实现,然后还有一些喂药等等这些需求。然后,下一步我们真正做人形的,可以搬运,可以牵扶。我们现在的行走机器人在深圳也注册了,做行走的技术,行走加上操作,加上很多的智能。这也是我们很多智能机器人终极目标,我想有这么大的需求,我们从单功能作起,多功能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还在努力。

张东(左)、席宁(右)
张东:
非常赞同张建伟的观点。我们机器人能在养老院、医院帮助病人有很长路要走,包括高效率的,轻量化关节机构并不成熟。但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里面包括陪伴型的一些这种带情感陪护的机器人,我觉得作为养老机构也是需要的。
第二个智能的轮椅,帮助老年人的出行。同时,我们一些智能护理床也能够帮助老年人在生活上提供很多的便利,包括一些翻身等等都是可以做的。从我们芜湖来讲,我们目前做了一些服务机器人,但是我们服务机器人主要还是一些2B机器人,进入家庭市场的话,我们觉得技术上还不完全成熟。
但是您刚才提的这些合作的建议,我想我们会努力做一些工作,争取未来能够有一个好的合作。谢谢。
刘进长:最后一个问题。

高端访谈现场
观众4:
我是做视觉方面研究的,我们发现视网膜上有三级管,非常有意思。我们认为大脑中也有很多三级管,这就解释人为什么跟Alphago下围棋的时候,耗电量是两万分之一。我自己感觉就是机器人会越来越像人一样,以后人也会越来越像机器一样,这两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需要比较远一点的时间,可能几十年,也可能十几年。我问的就是,如果机器人更像人的话,有哪些关键的方面需要改进的像人?因为我们发现人眼有颜色,黄金分割点,除了形状以外,我们可以让机器能够感知美,并且人眼用硬件实现感知,不是现在机器视觉的,用软件识别形状这些颜色,美不美。那么人眼是有硬件,就是大脑,视网膜上有硬件的通道,我们发现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模仿人的眼睛,让机器人也能看到美,在这是以有情感的机器人为基本的条件。机器如果像人的大脑一样,还有那些方面需要挖掘就更像人?
孙守迁:
我们最近正在做一个计划,就是创新设计大数据计划,也是中国工程院的计划。我们设法从五条路径把数据进行集成。第一个,各位擅长技术的数据,今天上午院士报告以及下午的报告,从技术路径来考虑,从信息,从机械、电子或者软件,还有一个信息路径就是从文化、艺术以及跟心理学、生理学这些数据,以及商业这些数据形成汇聚,使得构造成一个基于大数据的设计系统,这个工程很大。所以我们要汇聚数据,包括要汇聚当地河姆渡文化的数据,让这个系统更加能够有审美眼光,能够看到什么方案是美的。跟我们这个计划相关的,包括美国的公司,最近在做衍生设计,就是它自动不要设计师了,自己来形成方案,让高级设计师来判断。后来,前不久马云这边又出一个方案——“鲁班”设计系统,就是从大数据里形成这个方案。
这个系统假如告诉未来的机器人的话,可能初级设计师都要下岗。以后如果这个系统给机器人使用的话,那以后会怎么样?我们正在观望,但是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已经做了两三年了,再有两年以后,已经在做测试了,另外,会进一步用到工业界。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了关于美的判断,艺术方面的数据,我们也在进行汇聚。
我们德国的构成学说都是来自视觉方面的设计,元素、色彩、平面、立体,这些都对我们的人类的判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你们广东工业大学艺术学院的这些人有沟通,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往来。这里可能是另一个未来的大数据跟设计结合,可能会影响我们年轻设计师的未来。除了今天上午说到的对教师会有挑战之外,对设计师也会有挑战。我就先讲这些。
张建伟:
补充一下,刚才提到机器人2.0,我们人也变成了2.0的人,用很多机器人的技术,变成不是传统的人。这两个技术互相影响是我们推动机器人的一个技术的非常重要的源泉,现在内脑、感观和传感器,也是机器人跟国家的大脑计划相结合的非常重要的点。非常好。
黄广斌:
可我们的人工智能,其实跟脑不相关,不是一个脑袋,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另一个方向就是开始,就是脑神经研究已经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或者下一波也会起来,那么这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和脑科学进一步发展。
我们现在所说的识别,CPU这种识别,都不是人脑做的方法,新的趋势也会出现,将来的人工智能或者机器学习不要靠CPU,而是有点像新材料这种形式,这已经开始了。所以,你说的些我们一直在研究。我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微博上那个猫怎么看鱼、看东西,我在研究。
其实这个方向,我觉得未来十年之后应该会有更大的趋势。但是总体来说,人的脑袋,其实很复杂。人的脑袋和自然界有相似的地方,就是说自然界很美好的,总体有序,但是局部无序的。人的脑袋也是,所以人看上去一样,总体有序,局部无序;局部无序,又局部有序,很有意思。这部分如果真能打通,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应该是很好的促进。因为想机器人有很多的功能,不一定像人一样。其实,现在我们做的视觉和脑袋的视觉不一样,你提的方向应该是几年后有突破。一有突破,我就提醒做投资的这个方案有突破,估计有很多人要骂你了,因为另外一个新的机器视觉出现,原来那些可能都得关门倒闭。谢谢。

嘉宾提问
观众5:
非常荣幸有机会聆听各位高端专家的讲解。那么,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我一直非常的沉迷,包括我们公司,我和我的一群小伙伴都在往这个方向做努力。我想请教各位专家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了很久,就是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特别的火热,但是在落地的层面上其实还是有差距的。在很多的场合,很多专家提出人工智能落地的载体就是具体在哪些产业或者行业里能够有大的发展,或者说在近几年,三年五年里,比如智慧交通,比如医疗,比如教育,我想听一下各位专家自己的观点,就是三到五年里面,人工智能技术也好,机器人也好,在哪些具体的行业里面能够发扬光大?谢谢。
刘进长:做企业的想给你们投钱,哪一块可以落地?三五年能做什么?
张东:
我跟李总也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这块李总有很深的钻研,我们感觉到人工智能在近五年内能够落地的就是对我们工业机器人的帮助。因为我们工业机器人,实际上是往往是通过精确的视角,或者离线编程,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我们现在也在做这种工业的专家系统和解决方案,通过视觉自动识别,通过云端的相关工艺数据的调动,自动完成加工。这块我今天上午听了凯文·凯利的报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讲了一个观点,未来有可能创业的方式就是把知识放到云端,然后从云端进行学习,进行使用。我觉得在未来五年可能有大量的应用,这是我们下一代工业机器人的事情。
第二个我想讲的,落地的是在辅助驾驶这块。目前我也兼任芜湖市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组的负责人,那么现在无人驾驶在低速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受到了法律的限制。我们可以在一些密闭的环境里,比如停车场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无人的助驾,比如无人系统。用车载的辅助系统,我想在这块,应该说也猛攻到一个商业级的应用。我先谈这两点。
孙守迁:
我补充一下,我跟朱教授一起合作过,我们曾经搞过很多“河姆渡杯”中国小家电创新大赛,现在从小家电转向机器人了。我就向跟小家电的企业家们,其实你们可以做小家电+机器人,像今天上午的有一位国外专家做报告,小家电都有可能走向机器人。这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再次创业的机会。
另外,宁波市政府搞智能经济,里面也考虑智能装备,也就是小家电的生产装备,比如像伟利机器人在装配线上加机械手的做法,也给它带来新的增长点。小家电有很多这种生产线需要出口,甚至有的小家电企业就做生产线了,出口到越南。生产线上的机器人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可以大家进一步尝试。这都比较短线的产品,可能马上就可以落地的。我就提这点。
刘进长:
好,问题还有很多,专家们也还想回答很多的问题。但由于我看后边的一些同志们饿得抱着肚子,人是铁,饭是刚。一顿不能少吃。明天专家也都在,咱们可以私下交流。感谢各位,大家提问很精彩,回答也很精彩,我们再继续思考。